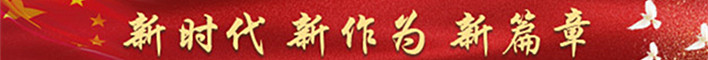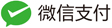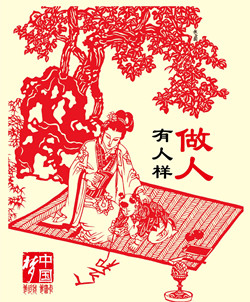这片多情的土地
来源:织梦技术论坛
作者:曾宪富
时间:2025-09-04
导读:曾宪富 土地,我从小到大,甚至是人到中年都一直在追寻,它给了我什么,我为什么又这么深深的爱着它 我在这片土地上生,在这片土地上长,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惦记着它,哪怕是给过我往日的沧桑岁月,还是刻骨铭心的酸楚,我永远不会忘记它,
曾宪富
土地,我从小到大,甚至是人到中年都一直在追寻,它给了我什么,我为什么又这么深深的爱着它……

我在这片土地上生,在这片土地上长,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惦记着它,哪怕是给过我往日的沧桑岁月,还是刻骨铭心的酸楚,我永远不会忘记它,更要想起它,毕竟它给了我挥之不去的酸甜与苦辣……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觉得我是一个怀旧的人,起码我到了年过半百的年纪还在对往日岁月的回忆,说明我不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人。说懂事,我只是一个多愁善感喜欢说起往事不堪回首,昨天的点点滴滴,在今天我记忆犹新,去捕捉,去记起,去回味,就是对自己人生之路的一次最好的回谢吧!

对这片土地的认识,还得从我的童年时光开始,五岁前我不知天文地理,五岁后我的启蒙,我的记忆还是托这片土地的某个角落。1958年,我的父亲从千年历史古镇下放到源潭公社黄盖大队源二生产队,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这次下放却把他永远的留在了那里,他在这里风雨飘荡的日子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伴随他生活了近三十年。命运也总是捉弄着人,他原本以为下放农村干上几年就会回去,可谁知父亲却独自一人过着吃集体饭,干集体活,自他找到了他生命的另一半,我们的母亲,这才让他彻底打消了回古镇的念想。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并不是不想知青回镇,其实他有难言之隐,以前我们不理解,后来我们才发现,父亲也是出自于对这片土地的不舍而选择继续留在这里,却不知,他的这份念想把他永远的放在了这里,以致于我只能用文字来记叙,来回味那难忘的岁月……
源潭历史可追溯至久远年代,见证了诸多朝代的更迭变迁。其建置历经多次变化,1952年置源潭镇,1958年属聂市公社,1961年为源潭公社,1984年又复置镇,2015年与乘风、聂市三乡镇合并再置镇,几十年来,合又分,分又合,分分合合,一次又一次的演译着时代的发展。自我们的先祖从江西搬迁过来,把我们一代又一代变成了这里的人。父母在一起后,我们兄弟姊妹也先后来到人间,在源潭街上那个叫“杨家咀”的老掉了牙,甚至是摇摇欲倒的公房(国家的)里便成了我们遮风避雨的家,从此我们就在这简陋的屋子里过着那清贫的生活。

对这片土地的熟知不是一天两天能透彻的,五岁前我不知世事,五岁后我开始走进我的思维,因为往事不堪回首,但我还是能清晰记得……源二生产队就盘居在杨家咀对面的堤垸里,三百多亩田地被“哑河”团团围住,形如椭圆状,受黄盖湖流域的影响,这里的田地是河水冲击而成,独特的资源,造就了土地的肥沃,可算得上是一个产粮的地方。大集体时,只有八岁的我,不知是时代造化人啦,还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时我每天除了上学就是放学看牛,弱不禁风的身子常常被牛拉着连滚带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让大人们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但能为家里挣上工分也是苦中有乐。
俗话说:隔山容易隔水难。我们住在街边,田地却在河对岸,那时没有修桥,每天干活都得从船码头坐上彭嗲彭妈划的木船,有时一天要来回坐六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里雨里从未间断过。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刚入青年都在这船上来回穿梭,直至后来离开杨家咀我才告别了这船。时过境迁,往事难忘。那个时候尽管日子过得很辛苦,我没有怨声载道,只是因每天早晚要赶船让我觉得很累,为了多做点事,我们有时是天刚濛濛亮就去坐船,可划船的人起得却没有那么早,要么就坐在船上等(划船人每天收工时都将船锁上了),要么就去划船人家去敲门,人家也并不是每次有求必应,只能在河边焦急的等待,只要见到划船人肩着木浆过来,我们都要跑过去把木浆接在手里,匆匆跑到船上架起木浆,好让划船人起锚撑向对岸……
大集体时,为了能为家里挣上几个工分,小小年纪的我学会了大人们干的活,插秧割谷不在话下,犁田整地常常被牛拉着两边摆,摔倒后又爬起,满身泥水还在不停地吆喝着,让牛走得更快,也好去耕下丘田。源二队十多户人家耕种着二三百亩田地,在那个没有机械,全靠双手劳作的年代,这么多田地要把它耕种好,其难度一想而知,没有起早贪黑,没有辛苦汗水是不可能完成上交任务的,后来,分田到户,我家五口人分到了十三亩六分田,我们虽然年纪小,但却很懂事,只想帮父母减轻负担,为家里多做些事已成了我们的共识。这分到的田却不在一处,各丘相距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有时是先把这丘田忙完了,又转向另外一丘田,犁耙工具肩扛手提,打谷的箱桶还得我与哥哥俩一前一后给肩着,弟弟也不是闲人,他拿着箩筐跟在后面跑,父母都是提前把秧苗育好,把哪丘田先种哪丘田后种都计划好,尽量不干费工活。这十三亩多田的收成,每年除去上交给国家外,五口人的温饱问题也解决了,庆幸自己摆脱了过去有上顿没下顿饭的日子。
时光在走,田园生活给了我们太多太多的乐趣,在源二队时,来了个从河南来的中年人,他姓张,他有一手种瓜的手艺,我们都叫他“张师傅”。记得队里把那靠近“哑河”边的三四亩地承包给他种,除去上交给队里的一部分,他每年还是可攒下一点钱,虽然不多,但我们常看到他把钱往老家寄,只是人到中年的他还是光棍一个,这大概也是他离家出走,漂泊在外的原因。他一口河南口音,说快了我们根本听不懂,正因这在后来的园边“偷”瓜时,尽管他喊破嗓子我们只当耳边风,我们压根儿也不知他嘴里说的什么,一点可肯定,他是不希望我们摘他的瓜吃,在那个瓜果缺乏的年代,能看到在源二队的地里长出的大西瓜,我们咱不唾唌欲滴的呢?好在他没有那么气势汹汹,我们调皮捣蛋也弄得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几个小家伙大口大口的把西瓜往嘴里吞,那神态令人啼笑颜开,其乐无穷!
在赞美这片土地的同时,我也被当时的自然灾害受到不小惊吓,屡屡回想起来,心背如拨冷水,阵阵阴凉。那个时候的河堤低矮单薄,如遇突发山涝洪水,堤身经不住浸泡决口是常事,已成了三年一大涝,两年一小淹,我们种植的农作物几乎是颗粒无收,洪水泛滥成灾,生活也变得困难重重,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酸楚的滋味真不好受,心想这自然灾害何时能止,辛辛苦苦种植的农作物不再打水漂。不能让水患肆无忌惮地致灾扰民,当时镇里就下决心将被洪水冲毁的缺口和低矮单薄的堤段进行抢修并加固,我们垸内的村民首当其冲,每家每户按田地和人头分到各自的担土任务。
那时候的每年秋收过后,村民们都在忙着抢修秋冬水利,我们家五口人年年都要分到几十百把方的担堤义务,父亲体弱多病,只能在家做些轻微的家务活,弟弟人小担不了土,母亲就带着我和哥哥,三娘崽拿着扁担箢箕和锄头来到离家几里之外的毛湾垸和土咀垸挑土筑堤,几十方土全靠肩挑,并是从堤下挑到堤上去,那时的我常常被肩上的扁担压着上气不接下气,两腿发软,腰酸背痛,好几次只想扔掉扁担跑人,但看到挑着泥土的母亲和哥哥拚命的往堤上跑,我只好打消念头,咬牙坚持,凭着初出牛犊不怕虎的干劲,硬是不把土石方任务完成决不收兵。为这,我的母亲很欣慰,她说她的二儿子“小兵伢”已经长大成人(其实我那时只有十三四岁,但在母亲的眼里心中我就是一个男子汉);为这,我的兄长,他说他的二弟“小兵”可以独挡一面,成了他的好帮手,好搭档。
这样的日子一直在继续,虽有些乏味与疲惫,但田野风光总是给我带来希望与梦想,只要不倒堤,农作物就能保住,收成好,日子过得也不紧紧巴巴,家里还有略余,我的小学,我的初中生涯都在与田地打交道,逢放学放假我就要跑到河那边的田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那时的我没有走出去,也不知外面的世界是啥样,有没有比田园更精彩的画卷,只要听爸妈的话,好好读书,勤快做事,梦里啥都有,人生之路还很长……
到了后来,这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毛湾垸整个堤身通过机械的推筑加宽加高,已固若金汤了,垸堤有保障,垸内有希望,年年都是鱼米满仓,丰收的景象洒满整个内垸,只见片片水稻飘香四溢,块块水塘鱼跃翻腾,丘丘水田虾尾摇摆,各类蔬菜应有尽有,乡亲屋前屋后鸡鸭翩翩起舞,栏里的肉猪欢蹦乱跳,挂满果子的树叶迎风飘扬,栋栋新房矗立而起,林荫小道宛如天路,乡亲们谈笑风生,好一幅山美水美,田美谷美,一切皆美的田园画面,如云卷云舒,世外桃源……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谁也不知道以后的事,今天已没有源潭镇这个名称了,在那轮乡镇合并的大潮中融入了聂市,也成了今天的聂市镇政府所在地,但那个杨家咀,那个源二队依然还在原地,只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然而在我生命中早已注入了血液,不可置换,更不可替代,它就是我生命的源泉,是我叶落归根的地方……
此时的源潭河傍街靠堤而过,只是在水利庵那个转弯的地方悄悄地流入了黄盖湖,沿途可见亮点纷呈,蔚蓝的天空朵朵白云片片团团,青青的河水被阳光照射得银光闪闪,水潺潺,浪花花,儿时与发小戏水的画面涌上心头,光着的身子,常常被鱼虾戏弄,既有酸酸,又不失风度,只把戏水当成是最美的喜爱,有时稍不留神,就被闻讯赶来的长辈手拿竹条吓着往水里钻,到最后换来的却是玩个不少,打个不了,细嫩的身子光屁股就留下一条条“彩虹”,好在这只伤皮不伤骨的家教法,让我们在水里学会了游泳,读懂了人生的不易。
这片土地造就了我们,始终滋润着我们,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点点滴滴,无不生机盎然,竞相绽放,日月星辰,光阴轮回,忘不了的乡情,理不完的怀乡思绪,总是缠绵着游子的灵魂,在一次次洗礼之后,这份情感愈来愈浓,愈来愈烈……
现在的我已离开家乡近四十年,只是这么多年,我从未忘记过那片土地,我的心一直都在惦记着,思念着,它给了我不可磨灭的记忆,我的生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只是现在每次回源潭多了一份情愫,走在那条熟悉的老街却多了些许的陌生面孔,我记得在进街口的那个源潭桥到现在的这条街的尽头,除了那些老户子那些老熟人我还有印象外,其他的都是未曾谋面,不过,我还是喜欢这条街,它给了我家的归宿,给了我儿时的记忆!
源潭街,巴掌大的位置,但它如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大街小巷不少,能叫上名字的也有好几个,河街、老街、中街、金狮坪、新正街、万家岭角等等,说是街,其实它不像城里的大街那么繁华,那么宽阔,那时的二层楼都不多,大都是一层平房,且紧挨着,墙连墙,开门就见,就如一家人。街虽然不大,但小店小铺遍街都是,各种小吃五花八门,最为爽口的是麻花、油条、碗糕、包子、馒头、小花片等等,就麻花和碗糕至今都是这里的地方招牌熟食,南来北往的人只要经过源潭街,就会打听这两道地方小吃,秤上二三斤,带回去让家人尝尝,还真是令人赞叹,令人回味。更有趣的是那个计划经济年代一些啼笑皆非的事,至今都还在我脑海里,时间越久,沉淀越深。那时购买物资,紧缺的,稀少的,吃香的都得凭票买,布票、油票、米票、肉票等等这些物资,如没有票那真的是只能望眼欲穿,欲买无门,为了这些购物票不知愁坏了多少人,伤透了多少心,最令我难以释怀的就是那肉票。一条街,一个食品站,一张肉板,要想吃肉,非得绞尽脑汁,变得法子弄到那票,否则只能看着人家吃肉你流口水。那时每家每户按人头分到少之又少的肉票,一家人平日里油水进得少,巴不得吃点肉开开味补补身,但一张票的购买量也是受到限制,人平几两肉,几筒骨,还没尝到味,碗里就是光光的了,这些都不说,令人头痛的莫过于凭票买肉时的尴尬场面。座落在公社下面的食品站是这个小镇上国营单位最香的一个,牲猪和鸡鸭蛋更抢手,唯有那每天早上购买肉时,这里成了小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在食品站的肉类销售店里,买肉的人排成长队,手拿肉票还不一定能买到肉,人多肉少,排在前面的,亲戚朋友的,熟人的可能会更幸运一些,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不但难买到肉,就是买到了的也是那点肥肉那点骨头,为这也发生过令人实在看不下去,而与营业员争吵的事,手掌刀“权”的营业员不以为然,但遇到正气“大侠”,他也只好甘拜下风,按理依规把秤砣提起,手起刀落,这才平息那买肉风波。时过境迁,但往事不能忘记,特殊年代,计划经济,我们只能顺时度日,慷慨行走……
这片土地,这个小镇故事太多,我想我就是写上十天八夜也写不完,道不尽,我更想我们每个人都会留恋自己的故乡,只是每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不同,但我想情怀大致都是一样,无论你在何方,不管时间有多长,你永远也走不出对故乡的思念,这就是情怀,是眷恋……
源潭,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写于2025年9月4日
责任编辑:朱书斋
上一篇:开笔添智,人生始立——黄金小学举行一年级“开蒙启智”仪式
下一篇:没有了
下一篇:没有了
相关文章:
栏目分类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